译典友情编辑(建议登录会员后操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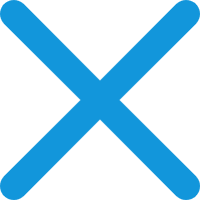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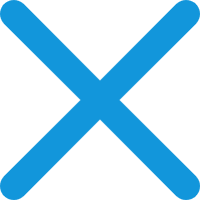
编辑说明:您可以直接修改编辑中英文词条(句子),也可以在备注栏输入补充解释和支持材料,甚至可以上传图片。您编辑的内容将以署名方式展示给其他用户。您的参与,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建议您先登录/注册本站会员,认领本词条的编辑权。译典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您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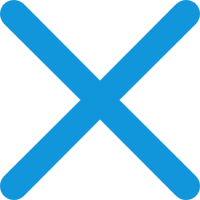
通译语典文库是一部经典文章集合。通过上下文来限定语句直至词语的语境, 获取最准确的语义,直达翻译佳境!
正文
目录
文库目录
文库收藏
中文百科
Wiki百科
<<快速查询:
属类:世界名著-
-[作者: 乔治·奥威尔]
-[阅读: 3320]


字+字-
页+页-
原文
这是四月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却又寒冷,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快步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低垂着头,想躲过阴冷的风,但动作还是不够快,没能把一股卷着沙土的旋风关到门外。
1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门厅那头钉着一张彩色宣传画,大得不适合钉在室内,上面只有一张巨大的面孔,宽度超过一米。那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蓄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面相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想坐电梯是没希望的,即使在情形最好时也很少开。目前白天停电,这是为迎接仇恨周的一项节约举措。温斯顿所住的公寓在七楼,他现年三十九岁,右脚踝上方还有一处因静脉曲张形成的溃疡,所以只能缓慢地走楼梯上去,中途还歇了几次。每层楼梯正对电梯门的墙上那张有着巨大面孔的宣传画从那里凝视着它是那种设计得眼神能跟着你到处移动的肖像画。“老大哥在看着你”,下方印着这样的标题。
2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在公寓里,有个洪亮的声音正在念一连串数字,跟生铁产量有关。此声音来自一块长方形金属板,它像一面毛玻璃面的镜子,嵌在右墙上。温斯顿扭了一下开关,声音多少低了一点,但仍清晰可闻。这个装置(叫做电屏)的声音能调小,然而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他的体形偏小,瘦弱,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工作服只是让他更显单薄。他长着一头浅色的头发,面色红润自然,由于寒冷的冬天刚刚过去,再加上长期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头的剃须刀片,他的皮肤显得坑坑洼洼。
3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即使隔着关闭的窗户,仍然可以看出外面的寒意。下面街道上,小股的旋风卷动尘土及碎纸螺旋上升。虽然出了太阳,天空也蓝得刺眼,但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似乎一切都没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色八字胡的脸从每个能望到两边的街角居高临下地盯着。正对面的房屋前面就贴了一张,印有标题“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眼睛死盯着温斯顿。下面临街处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已破,在随风一阵阵拍打着,把一个词一会儿盖住,一会儿又展开:“英社”。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间掠过,像苍蝇般在空中盘旋一会儿,然后划了道弧线疾飞而去。那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视人们的窗户。但巡逻队还不足为惧,足以为惧的只是思想警察。
4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传出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报有关生铁产量和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消息。电屏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高于极低的细语,就能被它拾音。而且不仅如此,只要他待在那块金属板的视域之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也能被看到。当然,在具体的某一时刻,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接进某条电线的频度如何以及按照何种规定进行,都只能靠臆测,甚至有可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个人。无论如何,他们可以随时接上你那条电线。你只能生活——确实是生活,一开始是习惯,后来变成了本能——在一个设想之下,即除非你处在黑暗中,否则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偷听,每个举动都会被细察。
5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温斯顿保持着背对电屏的姿势,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知道,即使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什么。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幢在一片不堪入目的地带拔地而起的白色大型建筑。这里——他略带几分厌恶地想道——这里就是伦敦,第一空域的主要城市。第一空域本身是大洋国人口第三大的省份。他绞尽脑汁,想找回一点童年记忆,以便让他记起伦敦是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满眼都是摇摇欲坠的建于十九世纪的房屋,侧墙靠木头架子撑着,窗户用纸板挡着,屋顶是波纹铁皮,破旧的院墙东歪西斜。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在挨过炸弹的地方,空中飞扬着灰泥和尘土,野花在一堆堆瓦砾上蔓生,还冒出许多龌龊的聚居区,也就是鸡舍一样的木板屋。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可是没用,他想不起来:他的童年除了一系列光亮的静态画面,什么也没留下,而那些画面都缺少背景,大部分也不可理解。
6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就是“真部”——跟视野中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它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水泥熠熠发亮。它拔地入云,一级叠一级,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刚好能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美术字体镌刻在真理部大楼正面:
7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战争即和平
8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自由即奴役
9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无知即力量
10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另外还有相应的地下附属建筑。此外只有三座外表及规模类似的大楼分散坐落在伦敦,周围的建筑彻底被那三座大楼比了下去,所以站在胜利大厦顶上,同时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分别为四个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就分工到了这四个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这四个部的名称用新话来说,分别是“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11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未去过仁爱部,也未曾进入过它的方圆半公里之内。那里闲人莫入,进去时,还要经过一段布着带刺铁丝网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道道钢门以及机关枪暗堡。甚至在通向它外围屏障的街道上,也有面目狰狞的警卫在转悠。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持两节警棍。
12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脸上已经换上了一副从容而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屏时,这样做是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走进那间很小的厨房。这个时间离开部里,就放弃了食堂的一顿午餐,他也知道厨房里除了一大块黑面包别无他物,得把它留到明天早上当早餐。他从架子上拿了个装有无色液体的瓶子,上面简单的白标签上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如同中国的米酒,它散发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油一般的气味。温斯顿倒了快有一茶杯,鼓了鼓勇气,然后像喝药一样一口气灌了下去。
13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马上,他的脸变得通红,眼里流出了泪水。那玩意儿像是硝酸,不仅如此,喝的时候还给人一种后脑勺挨了一胶皮警棍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胃里的灼热感消退了一点,一切好像没那么难受了。他从印有“胜利香烟”的压扁了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不小心把它拿倒了,烟丝因此掉了出来。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了点。他回到起居室,在位于电屏左侧的一张小桌子那里坐下来。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四开大的空白厚本子,它的封底是红色的,封面压有大理石纹。
14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不知为何,起居室里的电屏安装的位置不同寻常。它通常在远端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这张电屏却安在较长的那面墙上,正对窗户。电屏一侧有个浅凹处,温斯顿就坐在这里。建这幢公寓楼时,这地方很可能原意是用来摆书橱的。温斯顿坐在这个凹处,尽量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屏的视域范围之外。当然,他的声音仍会被听到,不过只要待在目前的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他之所以想到这会儿要做的这件事,部分原因就是这房间不一般的布局。
15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同样让他想到做这件事的,还有他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是本异常漂亮的本子,纸质光滑细腻,因为岁月久远而变得有点泛黄。那种纸至少已经停产了四十年,因而他估计那本本子的年份远不止四十年。他在一间肮脏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看到它,那间铺子位于市内某个贫民区(究竟是哪个区,他现在不记得了),当时他马上有了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拥有它。党员不应该进入普通店铺(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买卖”),但这一规定未被严格执行,因为许多东西——如鞋带和剃须刀片——除非去那里,否则就买不到。他往街道左右两个方向迅速瞄了瞄,然后溜进去花两元五角钱买下了它,也没想它能派什么用场。他知错犯错地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带回家,上面就算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有违原则。
16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他准备要做的,是开始写日记,这不算是件非法的事(没什么是非法的,因为不再有法律),然而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惩罚会是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劳改。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脂。钢笔是种过时的东西,就连签字时也很少用,他偷偷摸摸、而且是费了些事才得到一杆,只是因为他感觉那种漂亮细腻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钢笔尖在上面书写,而不是拿蘸水笔划拉。其实他还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写很短的便条,他通常什么都对着口述记录器口授,对目前想做的这件事而言,当然不可能那样做。他把钢笔蘸在墨水里,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他感到全身一阵战栗,落笔是件决定性行为。他以笨拙的小字体写道: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17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他往后靠着坐在那里,陷入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中。首先,他对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完全没把握,不过可以肯定是那年前后,因为他对自己是三十九岁这点很有把握,而且相信自己是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在确定年份时,不可能没有一两年误差。
18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突然,他想起一个问题,他写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未出生的人。他的心思围绕那可疑的年份转了一会儿,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想起新话里的“双重思想”一词。他第一次想到此举的艰巨性:你怎样去跟未来沟通?从根本上说这不可能。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此情况下,未来也不会听他说;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他的预言便将毫无意义。
19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他对着那张纸呆看了一会儿。电屏里已经换播刺耳的军乐。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忘了他本来想说什么。在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从未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笔不难,需要做的,只是将他大脑里没完没了、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行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这一刻,就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另外,那处静脉曲张的溃疡又痒得难受,可是他不敢搔,因为一搔就会红肿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踝上方的皮肤痒、电屏里尖锐刺耳的音乐和喝酒造成的一丝醉意,他别无感觉。
20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突然,他完全是慌里慌张地写起来,但他对正在写下的东西并非全然心里有数。他用儿童式的小字体在纸上随意写着,一开始漏了大写,到最后连标点也不用了:
21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一部是关于一艘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轰炸的故事。观众很开心地看着一个胖男人奋力游泳逃离一架直升飞机追赶的镜头。一开始看到他像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扑腾,然后是通过直升飞机上的瞄准器看到他,接着他全身都是枪眼,他身体周围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沉下去,好像枪眼导致进水,观众在他下沉时大声哄笑。然后看到的是一条坐满儿童的救生艇,上面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个可能是犹太人的中年妇女坐在船头,抱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尖叫,把头深深扎进她怀里,似乎想在她身上钻个洞而那个女人用胳膊环着他安慰他尽管她自己也已经害怕得脸色发青,她一直在尽量掩护着他似乎以为她的双臂能为他挡住子弹。然后直升飞机往他们中间投下一个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道强光小艇变成了碎片。接着是个拍得很清晰的镜头是个小孩的手臂往空中飞得高高安在直升飞机前端的摄影机肯定在追着它拍从党员座位那里传来一片鼓掌声但在群众席那里有个女人突然无故喧哗起来嚷叫着说他们不该放给孩子看他们做得不对别放给小孩看直到警察去把她架了出去我不认为她会有什么事谁也不关心群众说什么群众的典型反应他们从来不会——
22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温斯顿停下笔,部分原因是肌肉痉挛。他不知道是什么让他的笔尖流淌出这些垃圾东西。然而奇怪的是,写这些东西时,他脑子里清清楚楚记起了另外一件事,以至于他几乎也想把它写下来。他意识到就是因为这另外一件事,他突然决定回到家里并从这天开始记日记。
23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如果那样模糊的一件事也能称为发生过,那么它是发生在那天上午,在部里。
24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当时快到十一点了,在温斯顿所在的档案司,人们开始从小隔间里往外拉椅子,摆在大厅中间,正对着大电屏,这是为两分钟仇恨会做准备。温斯顿正要在中间一排某个位置就座,有两个他只是面熟,但从未说过话的人出乎意料地来了。其中一位是个女孩,他经常在走廊里跟她擦肩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她有时两手都沾着油,还拿了个扳手——她负责某部长篇小说写作机的机械维修工作。她是个样子大胆的女孩,差不多二十七岁左右,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有雀斑,动作像运动员那样敏捷。一条窄窄的鲜红色饰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程度刚好能显现出她臀部的优美线条。从第一次看到她的那刻起,温斯顿就讨厌她,他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她随时随地营造的那种代表着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和完全心无杂念的氛围。他几乎仇恨所有女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人——特别是所有的年轻女人——总是党最死心塌地的信徒、轻信宣传口号的人、业余侦探和异端思想的包打听。但这个女孩给了他一种印象,就是她比绝大多数女人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她迅速瞟了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刺进他体内,并注入一种黑色的恐惧感。他脑子里甚至想到,她有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种机会微乎其微,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仍会让他感觉特别不自在。这种感觉混合了敌意,还有恐惧。
25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另外一位是个男的,名叫奥布兰,是名内党党员。他的职务重要而不可测,温斯顿对其性质只是略有感觉而已。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内党党员走过来时,椅子周围的这群人中出现了片刻的肃静。奥布兰高大结实,脖子很粗,面容粗糙,为人幽默而又冷酷。虽然外表让人望而生畏,但他的举止有一定的魅力。他有一招,就是推一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这个动作很奇怪,能让人解除戒心——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奇怪地给人以文质彬彬的感觉。如果还有人这样想的话,这个动作也许能让人想起一位十八世纪的贵族在邀请别人用他的鼻烟。十几年来,温斯顿见到奥布兰的次数可能差不多也就是十几次。他感到奥布兰对他而言很有吸引力,不仅因为后者温文尔雅的举止与职业拳击手块头的反差让他觉得很有趣,更因为他有个秘密信念——也许根本不是信念,而是一丝希望,即奥布兰在政治正统性方面并非完美无瑕,他的表情无疑说明了这一点。话又说回来,也许他脸上表现出的根本不是非正统性,只不过是智慧。但不管怎样,从外表上看,他是那种可以谈谈心的人,如果有办法躲过电屏跟他单独在一起的话。温斯顿从未付出一点努力去证实这种猜测,确实,也没办法证实。那时,奥布兰看了一眼手表,看到马上快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跟温斯顿坐在同一排,中间隔了几张椅子,一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坐在他们中间,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隔间工作。那个黑头发女孩正好坐在温斯顿身后。
26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这时,大厅那头的电屏里突然传出一阵令人难受的刺耳讲话声,如同一台巨大的机器在缺少润滑油的情况下运作时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能让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仇恨会开始了。
27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照例,当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这个人民公敌的面孔闪现在电屏上时,观众发出此起彼伏的鄙夷之声,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带着恐惧和厌恶发出一声尖叫。戈斯坦因是叛徒和蜕变者,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有多久)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几乎跟老大哥平起平坐,后来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然而又神秘地逃走并藏匿起来。两分钟仇恨会的进程每天都不一样,但无一例外,每次都以戈斯坦因为主角。他是头号卖国贼,是最早破坏党的纯洁性的人,所有后来对党所犯的罪行、变节、破坏活动、异端邪说以及越轨行为都直接出自他的煽动。在某个地方,他仍活在人世并策划着阴谋:也许在大洋彼岸,在豢养他的外国主子的保护之下,也许甚至——时不时会传出这种谣言——就潜伏在大洋国本国的某处。
28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温斯顿感觉胸口发闷。每次看到戈斯坦因的面孔,他都会有百感交集的痛苦感觉。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面孔,头顶有一圈浓密的白头发,毛茸茸的,下巴上蓄着一小撮山羊胡——这是一张聪明人的面孔,但不知为何,从本质上让人觉得可鄙。靠近他又细又长的鼻尖处,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年迈昏庸的感觉。这是一张类似绵羊的脸,就连声音也像绵羊。戈斯坦因在一如既往地恶毒攻击党的各种教义——这种攻击夸张而荒谬,连小孩子都能看穿,但又刚好貌似有理得会让人警惕,即其他头脑没那么清醒的人有可能上当受骗。戈斯坦因侮辱老大哥,谴责党的独裁,要求马上与欧亚国和谈,他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已被背叛——全是以快速和多音节的方式讲出来,是对党的演讲家那种惯常风格的拙劣模仿,甚至也包含新话——没错,比任何党员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使用的新话还要多。而且自始至终,为避免人们可能对戈斯坦因那貌似有理、哗众取宠的讲话所掩盖的事实有所怀疑,电屏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数排着纵队的欧亚国军队在前进——那是一排又一排长得很壮实的人,有着缺乏表情的亚洲人面孔。他们涌现到电屏上,然后消失,代之以其他长相完全类似的军人。单调而有节奏的沉重军靴声成了戈斯坦因那咩咩叫声的背景声。
29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仇恨会进行了还不到半分钟,房间里有一半人发出了不可遏制的怒吼。那张自鸣得意、绵羊脸一般的面孔以及这张面孔后面欧亚国军队那可怕的力量令人无法忍受,再者,看到或甚至想到戈斯坦因,就能让人们不由得感到恐惧和愤怒。他比欧亚国或东亚国更经常成为仇恨对象,因为大洋国跟这两大国中的一个进行战争时,一般跟另一大国处于和平关系。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戈斯坦因被所有人仇恨、鄙视,尽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的理论每天上千次在讲台、电屏、报纸、书本上被批驳、被粉碎、被嘲笑、被一般人认为是可鄙的垃圾,然而这一切似乎从来没能让他的影响降低过,总会有一些新的上当受骗者在等着被他诱惑,每天都有奉其指令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挖出来。他是一支巨大的影子部队的司令,那是由力图颠覆国家的阴谋制造者所组成的地下网络,这个网络的名称据说叫兄弟会。另外,还有一些悄悄流传的说法,是关于一本可怕的书的。它汇集各种异端邪说,由戈斯坦因所写。这本书到处秘密流传,没有名字,人们在不得已提到它时,简单称之为“那本书”。不过人们都是通过不清不楚的谣言得知这些事情,凡是一般党员,都会尽量避免谈及兄弟会和“那本书”。
30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进入第二分钟,仇恨会达到了狂热状态。人们在座位上跳上跳下,用最大的嗓门叫喊着,想盖过电屏里传来的发狂的咩咩叫声。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脸色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像条离水的鱼。就连奥布兰那张严肃的脸庞也涨红了。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健硕的胸膛气鼓鼓的,还在颤抖,似乎正在忍受波浪的冲击。温斯顿后面的那个黑头发女孩开始喊:“猪猡!猪猡!猪猡!”突然,她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掷向电屏,打中戈斯坦因的鼻子反弹回来,但那个声音仍然无情地响着。很快,温斯顿发现自己在和别人一起呼喊,用脚后跟猛踢所坐椅子的横档板。两分钟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过上二十秒,任何装扮都变得毫无必要。一种出于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可怕情绪,一种去杀戮、拷打、用大锤去砸人脸的渴望像电流般通过整个人群,将一个人甚至是违背其意愿地变成面容扭曲、尖叫不止的疯子。但他们感到的那种愤怒是种抽象而盲目的感情,因此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转向戈斯坦因,恰恰相反,而是向着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电屏上那个孤独的、被嘲笑的异端分子,他是在充满谎言的世界上真理与理智的唯一守护者。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一刻,他跟周围的人们站到了一起,对他来说,他们所说的关于戈斯坦因的一切全都属实。那些时候,他对老大哥私下的厌恶变成了崇拜,而老大哥好像高高屹立,是位所向无敌、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岩石般矗立着,对抗亚洲的群氓。而戈斯坦因,尽管他孤立无援,甚至他本人是否存在都尚存疑问,但他仍像个阴险的巫师,仅仅凭借话语的力量,就能将文明的架构摧毁。
31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有时,甚至有可能故意为之地将个人的仇恨目标转来转去。突然,就像在噩梦中猛然用力把头从枕头上扭到另一边,温斯顿成功地将对电屏上那张面孔的仇恨转移到他身后那个黑发女孩身上。他的脑海里出现了生动的幻觉:他会用胶皮警棍把她殴打至死,会把她脱光衣服绑到一根木桩上,然后向她射满一身的箭,正如那些人对圣塞巴斯蒂安所做的;他会强奸她,然后在高潮之际割断她的喉咙。另外,他也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无法做到,因为她那可爱的柔软腰部——像是在请人去搂——围着的却只是一条可恶的鲜红色饰带,那是代表贞洁的咄咄逼人的标志。
32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仇恨会达到了高潮。戈斯坦因的声音变成真正绵羊的咩咩叫声,有那么一阵子,那张脸也变成了绵羊脸。接着绵羊脸渐隐于一个似乎在冲锋的欧亚国士兵形象之上。他身材高大,面目凶恶,手里的冲锋枪在吼叫着,整个人似乎要从电屏里跳将出来,以至于前排有几个人真的在座位上往后缩。然而正当此时,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敌军形象隐没在老大哥的面孔里,黑头发,黑色八字胡,充满力量和神秘的安详感,它大得几乎占据了整张屏幕。谁都没听见老大哥说什么,无非是几句鼓舞士气的话,这种话在一片嘈杂声中说出来,人们听不清都说了什么,然而仅仅说出这些话,就能恢复他们的信心。
33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然后老大哥的面孔又渐渐隐去,党的三条标语以醒目的大写字母出现了:
34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但老大哥的面孔似乎在电屏上又持续出现了几秒钟,似乎对每个人的眼球所造成的冲击过于强烈,不能马上消失。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扑在她前面的椅子靠背上,双手向电屏张开,嘴里还咕咕哝哝地颤声说些什么,听来似乎是:“我的大救星啊!”接着,她用手捂住脸,显然在祈祷。
35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就在此时,整群人发出了低沉缓慢而又有节奏的呼喊:“B——B!……B——B!”一遍又一遍,非常缓慢,两个“B”中间有长长的停顿,不知为何,很奇怪,有点野蛮的味道。在这样的背景声中,似乎能听到赤脚跺地和手鼓的咚咚响声。在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这样呼喊着。这是种情绪极其强烈时经常能听到的压抑声音,从一定程度上说,它类似对老大哥的智慧和威严的颂歌,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是种自我催眠行为,是制造有节奏的噪声以失去知觉的故意行为。温斯顿似乎感到五内俱寒。两分钟仇恨会时,他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和大家一起疯狂,但这种不似正常人所发出的“B——B!……B——B”的呼喊声总让他十分惊骇。当然,他也跟别人一起呼喊,不这样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感觉,控制自己的表情,做别人在做的事,这些都属于本能反应。然而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的眼神有可能泄露了感情,这可想而知。正好就在那一刻,那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它的确发生过。
36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就在那时,他和奥布兰四目相望。奥布兰已经站起身,刚才他把眼镜取了下来,那时正以他特有的动作戴眼镜,然而就在他们四目相望的不到一秒钟时间里,温斯顿就在那一刻知道了——对,他知道了!他知道奥布兰在跟他想着同样的事。一个确凿无误的信息已经传递过来,似乎两人的大脑都打开着,通过眼睛,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流入另一个人的大脑。“我跟你一样,”奥布兰似乎在对他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嫌恶,我全知道。不过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接着那心领神会的片刻转瞬即逝,奥布兰的脸色变得和别人的一样,不可测知。
37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可是他已经开始对这件事是否发生过没有把握了。这种事情永远没有后续,所起的全部作用,不过是让他在内心保持一种信念或希望,即除了他自己,还有别的人也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大规模地下串联活动的谣言说到底确有其事——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虽然总有没完没了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但要想确定兄弟会是否确实存在仍属不可能,有时他信其有,有时他信其无。没有证据,只有星星点点之事,可能其中有文章,也可能没有什么意思:无意听到的谈话片断,厕所墙上语焉不详的涂鸦,可能被当做接头信号的一个不起眼的手势。全是臆测而已,很可能一切都是他的想象。他回到他的小隔间,没有再看到奥布兰,他几乎从未产生要延续他们那一瞬间接触的念头,即使他知道怎样进行,也会危险之至。他们含含糊糊地对望一眼,只有一秒钟或者两秒钟,全部经过如此而已。但纵然如此,在一个人不得己而置身其中的与世隔绝的孤寂中,那也值得铭记。
38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温斯顿把身子坐直了一些。他打了个嗝,酒气会从胃里泛了上来。
39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他又定睛看那张纸,发现在无助沉思的同时,他也在写字,像是种自动行为,而且写得也不像刚才那样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他的钢笔在光滑的纸上写下了漂亮的印刷体大字,字母全部为大写:
40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打倒老大哥
41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张纸。
42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他无法不感到一阵恐慌,这没道理,因为写下那些字和开始记日记比起来,并非更危险,可是有那么一阵子,他想撕掉写了字的那几页,彻底放弃写日记这一危险举动。
43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没用。不管他是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忍着没写,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停止写,都没有区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他已经犯下了——即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仍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永远掩盖的,你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仍然注定会抓到你,迟早而已。
44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总是在夜里——逮捕无一例外在夜里执行。睡觉时突然被惊醒,粗暴的手摇晃着你的肩膀,电筒照着你的两眼,一圈冷峻的面孔出现在床周围。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没有关于逮捕的报道,人们只是失踪了,总是发生在夜里。你的名字被注销,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被清除,不承认你一度存在过,然后就被遗忘。你被铲除了,消灭了——人们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
45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有一阵子,他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里,开始潦草地写道:
46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从我的脖子背后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从你的脖子后面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
47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他又往后靠着坐在椅子上,有点为自己感到惭愧,于是放下钢笔。这时候他猛然一惊:有人敲了一下门。
48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
这就来了!他像只耗子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徒劳地希望不管那是谁,就让他试着敲下门就走吧。然而没有,敲门声还在继续。最坏的做法便是拖延。他的内心直打鼓,不过他脸上很可能没有表情,长期习惯使然。他站起身,脚步沉重地走向房门。
49

读书笔记
是否公开会员文库收藏夹,将感兴趣的文章收录此处。注册会员即可以使用此功能
- 加入书架
-
回顶部
- 上一页阅读背景
- 下一页
-
回底部
译典文库友情编辑(建议登录会员后操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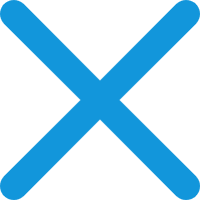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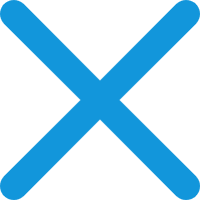

简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