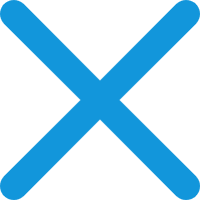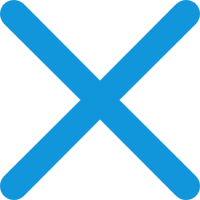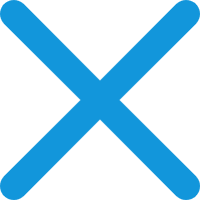三月间,我的生日到了,那以前学校发生的一切我都掠过不谈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斯梯福兹比过去更令人仰慕敬佩。如果不提前,学期结束时他就要离开了。在我眼里,他比以前更朝气蓬勃,更独立不驯,因此也更使人着迷。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心中只留下那时的那件大事的印象,对其它的那些较小的事的记忆似乎都被它吞没了。
1

我甚至难以相信自我回到萨伦到我生日这其间竟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只能认为这样是因为我知道事实应当如此;否则我会深信这两件事之间并无间隔,它们是接连而至的。
2

那是怎样的一天,我对此记得多清楚呀!我还能感到那天弥漫在空中的雾气;我还能透过那雾看到幽灵般的冷霜;我还能感到被霜打湿的头发垂到我脸上;在那个雾气沉沉的早上,一根流着蜡泪的蜡烛幽幽点燃在-一陰一-暗的教室里供照明之用,我还在那里张望,能看到同学们呵气暖和手指和跺地板取暖时呼出的白气在那清冷的空气中盘旋缭绕。
3

吃过早饭,我们已被从一操一场带进了教室后,夏普先生走进来说:
4

5

我心想准是皮果提又送来好多些吃的了,所以听到这命令心中为之一振。我附近的一些学生在我慌慌张张离开座位时还请我分发好东西时千万别忘了他们。
6

“别着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我的孩子,来得及呢,别着急。”
7

如果我当时有点头脑的话,就会对他说话时那动感情的语调有些奇怪了;可我当时想都没想。我急急忙忙来到客厅,看到克里克尔先生坐在那儿吃早餐,他面前放着一份报纸和那根棍子,克里克尔太太手里拿着封打开了的信。但是那儿没有一大包一皮吃的。
8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带到一张沙发前和我一起坐下,并说道,“我要和你很好地谈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9

克里克尔先生当然是我一直在注视的,他这时摇了摇头,并不朝我看,还用很大一块黄油烤面包一皮塞住嘴而止住了一声叹息。
10

“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世界每天有变化,”克里克尔太太说,“也不知道人们是怎样在这世界上逝去。可是我们人人都得知道这事,大卫;我们有的在年轻时就知道了,有的上了年纪后才知道,而有的一生都知道。”
11

12

“你在假期结束离家返校时,”克里克尔太太停了一会又说,“他们都好吗?”又停了一会,“你一妈一妈一好吗?”
13

不知为什么,我发一抖了,但我仍然热切地看着她,不愿回答。
14

“因为,”她说,“我很伤心地在今天早上听说,你一妈一妈一病得很重。”
15

在克里克尔太太和我之间升起一层雾,她的身影似乎在那雾后动了一下。然后,我感到滚一烫的泪水顺着我脸往下淌,接着她的身影又不晃动了。
16

17

18

19

根本不必这么告诉我。我已经伤心地大哭了起来,我感觉得到我已是这么一个广漠世界上的一个孤儿了。
20

她对我真是好极了。她一整天把我留在那里,有时让我在那儿单独呆呆;我哭,哭累了就睡觉,睡醒了再哭。当我再不能哭时,我就开始想了,这时我心头的压力重到无以复加,我的悲伤是那样一种无法缓解的钝痛。
21

可我的思绪是纷乱懒散的,我并没有专注地去想压在我心头的不幸,只是围绕着这不幸在纷乱懒散地胡想。我想到了我们那幢寂静关闭的房子。我想到那婴儿,据克里克尔太太说也早就日益虚弱了,他们相信他也会死。我想到我们住宅附近墓地上我父亲的坟墓,想到在那棵我十分熟悉的树下躺着的母亲。剩下我一个人在那儿时,我站到一张椅子上照镜子,看到我的眼睛好红,我的脸好凄苦。过了几个小时后,我考虑这样看来也许我的眼泪真的流不出来了。还考虑当我走到家门口时——因为我要回家参加葬礼——我失去的亲人有什么最使我想起来感动。我意识到在全体学生中我获得尊严感,由于我的伤心我已成为重要人物了。
22

如果有孩子真正感受到彻心的悲痛,那我就是一个。可我记得这重要一性一*于我是种得意——那天下午,别的学生都呆在教室里时,我却在一操一场上散步。他们上课时,我看到他们向窗外朝我看,我觉得我与众不同,便更加愁容满面,步子也迈得更慢了。放学后,他们出了教室和我说话,我觉得我那样真好——一点也不对他们表现出骄傲,和以前一样地注意他们每个人。
23

我要在第二天夜里回家,但不是乘邮车,而是乘一种很笨重的夜班车。这种车又叫“农夫”,因为主要是供在行驶区间做短途旅行上下的农夫用的。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故事,特拉德尔坚持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至今不知道他当时认为那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不过,这是他当时唯一可出借的东西,可怜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画满了骷髅的信纸,分别时他把这张信纸送给我,以使我的悲伤能从中得到安慰,并帮我获得安宁。
24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萨伦学校。当时我没想到我这一离开就再没回来。我们慢慢走了一整夜,直到早上九、十点钟才到雅茅斯。我往车外看,想找到巴吉斯先生,可他不在那儿;倒是一个胖乎乎、呼吸急促而看上去挺快活的小老头在那儿。这小老头穿着黑衣,短裤齐膝处飘着些褪色*的丝带,他穿的袜子也是黑的,还戴着大宽边礼帽。他大喘气地走到车窗前说:
25

26

27

“请跟我走吧,少爷,”他拉开车门说,“我将很荣幸地送你回家。”
28

我把手放进他手中时,一面揣摸一他是谁。我们来到一条窄街上的铺子里,铺门上写着:欧默,专营布料,成衣,衣饰,丧事用品,等等。这家店铺一逼一仄,令人透不过气来,里面放满了各种做好和没做好的衣,还有一个橱窗,里面放满了大礼帽和女式软帽。我们走进铺子后的一个小客厅里,看到三个年轻女人正在用堆在桌上的一大些黑色*衣料做着活,地上尽是些布头。屋中间有个烧得很旺的大火炉,还有一种一逼一人的气味,那是些热一烘一烘的黑绉纱发出来的气味;当时我可不知道那是什么味,现在才明白的。
29

那三个看起来又勤快又舒心的年轻女人抬头看看我又继续做手头的活。一针针,一线线。这时,窗外小院那一头的一个作坊里传来很有规律的铁锤声:“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一点变动也没有。
30

“嘿!”我的引路人对那三个年轻女人中的一位说道,“你们做得怎么样了,明妮?”
31

“在试衣的时候我们能完工”,她头也不抬,愉快地答道,“别担心,父亲。”
32

欧默先生摘下宽边帽坐了下来,大口喘着气。他太胖了,得先喘上一阵才能说:
33

34

“父亲!”明妮开玩笑说,“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海豚了!”
35

“嘿!我不知道怎么是这样,我亲一爱一的,”他对这问题想了想这样回答道,“我是挺那样的了。”
36

“你是那么一个心宽的人,你知道,”明妮说,“你对一切都能看得开。”
37

38

“是没用,真的,”他的女儿答道,“我们在这里都很开心,感谢上天!对不对,父亲?”
39

“我希望是这样的,我亲一爱一的,”欧默先生说,“现在我喘过气了,那我想我要给这年轻的学者量身一子了。请进铺子去吧,科波菲尔少爷。”
40

我按欧默先生的要求,走在他前面。他给我看了一卷衣料,说那是高级货,要不是为父母服丧用,那就再好不过了。然后他量了我的各种尺寸,并记在一个本子上。他记尺寸时,叫我看他的存货,有的款式据他说是“刚流行”,有的款式他说是“刚过时”。
41

“为这,我们时不时要亏点钱呢。”欧默先生说,“可是款式和人类相像呀,没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或怎样来的,也没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或怎样走掉的。在我看来,一切都象人生,如果你从那个观点看的话。”
42

我太悲哀,无法对那问题进行讨论,无论怎么说,也没法讨论那问题;欧默先生吃力地喘着气把我带回了客厅。
43

这时,他向一扇门后一道很陡的台阶下叫道:“把茶和黄油面包一皮拿来!”在那两样东西拿上来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坐在那儿向四周张望,并听着屋里穿针引线声和院里那边由锤子敲打出的音调。那两样东西被只盘子端上来,是专为我准备的。
44

“我已经认得你,”欧默先生看了我几分钟后说,而在那几分钟里我并没对那份早餐怎么在意,因为那些黑色*的东西已把我的胃口败坏了,“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年轻的朋友。”
45

46

“打你出生起,”欧默先生说,“我可以说在那之前。我在认识你之前认识你的父亲。他身高五呎九时半,占地二十五呎。”
47

“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从院子那边传来这声音。
48

“他占地二十五呎,如果他占了其中一小块地的话,”欧默先生很和善地说,“那不是他的要求就是她的指示,我不记得了。”
49

“你知道我的小一弟一弟怎么样了吗,先生?”我问道。
50

51

52

53

54

“别多想你无能为力的事,”欧默先生说,“是呀,那婴儿死了。”
55

听到这消息,我的伤口又裂开了。我离开那份我几乎没尝一口的早餐,走到那间小房间的一个角落的一张桌子前,把头靠在那儿,明妮忙把那张桌子收拾好,要不,放在那上面的丧服就会被我的眼泪弄脏了。她是模样好脾气也好的女孩,她轻柔慈一爱一地把我的头发从我眼睛上拨一开;可她和我完全不同,她此时因就要按时完成活计了而很快活。
56

这时,那锤子声也止住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从院子的那边走到这屋里。他手拿一把锤子,嘴里衔着许多小钉子。他得先把这些小钉子从嘴里拿出来才能说话。
57

58

59

60

“什么!昨晚我在俱乐部的时候,你就点着蜡烛干的吗?
61

62

“是的”约拉姆道,“因为你说过,把那干完后,我们可以一起做次短短的旅行——明妮和我——还有你。”
63

“哦!我以为你要把我排除在外呢,”欧默先生说着大笑起来,直到笑得咳嗽起来。
64

“——因为你这么好心地说了那一话,”那小伙子继续说,“我就挺心甘情愿地去干,你看就是这样。你能把你对它的看法告诉我吗?”
65

“我会的,”欧默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亲一爱一的,”他停下来转身对我说,“你愿意去看看你——”
66

67

“我觉得这样做也许并非不合适。我亲一爱一的,”欧默先生道,“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68

我也说不出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去看的是我无比亲一爱一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没看到过任何人制做那玩艺,也从没看到我所知道的棺材,但当那声音不断响时,我就想到那是什么声音;当那小伙子走进来时,我就确信他做的是什么了。
69

那两年轻女子(我还不曾听说她们的名字呢)干完手上的活后,又刷掉衣上沾的线头,便去店堂里收拾,准备接待顾客。明妮留在后面,把她们做好的东西折好,放进两只筐里。她一边跪着折衣放衣,一边小声哼一支轻快的小曲。她忙着干活时,约拉姆——我已确信他就是她的心上人了——走了进来,冷不丁亲了她一下(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我就在一旁),并告诉她,说她父亲已吩咐套车,他得马上准备好。然后他又走出去,她就把顶针和剪刀放进口袋里,把那穿了根黑线的针仔细别在她长袍的前襟上,再利索地穿上外套。从门后一面小镜子里,我看到映在那里的她那张喜气洋洋的脸。
70

我坐在屋角的桌子旁,一手支着头,一边看着这一切、一边想着完全不同的另一些事。马车马上就来到店门口,先被放上车的是两只衣筐,然后是我,再就是那三位。我记得那是辆客货两用的车,漆成很-一陰一-郁的颜色*,由一匹长尾巴的黑马拉着。车厢里就坐着我们几个实在太宽敞了。
71

想到他们当时乘车的原因,看到他们那么快活地坐在车上,我想我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和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奇怪感觉(也许,我现在世故多了)。我不生他们的气;我好像被扔到一些与其毫无半点沟通可言的东西中间一样,对他们更加生畏了。他们好不快活。那年长的坐在车前部赶车,那两年轻的就坐他后面,他对他们说话时,他们就马上趋身向前,分别俯在他那张大胖脸的两侧,很注意地听,要不是我那么退缩,他们也会和我交谈的。可我心情沮丧地坐在一角。他们的调一情和恣情把我吓住了(虽然那还远远够不上是喧闹),我几乎奇怪——居然他们不因那铁石心肠而受到任何责罚!
72

于是,他们停下来喂马,吃喝开心时,我应坚持禁食而不去碰他们碰过的东西。所以,一到家,我就尽快地从后面爬下马车,这样,就不至于和他们一起在那仿佛看着我的肃穆窗子前了,那些窗子一度曾那么明亮亮而现在却好像搭下了眼皮。哦,看到我母亲房间的窗户时,还有那个在好时光时曾是我的窗户时,我先前为回来时什么能让我流泪而一操一心是多么不必要的了!
73

我还没走到门口,皮果提就抱住我,把我带进了房子,一看到我,她就悲痛迸发,但她很快控制了,只低声和我说话,轻轻走路,好像怕死者受到惊扰一样。我发现她已很长一段时间没上过床了。她整夜地坐在那里不动,守候着。她说,只要她的那位可怜又可一爱一的美人还留在这地面上,她就决不会离开她。
74

我走进客厅,默德斯通先生在客厅里,可他并没注意到我,只是坐在火炉边的扶手椅上默默流泪,默默深思。在铺满信件和文件的书桌旁坐着正忙着的默德斯通小一姐,她向我伸出凉凉的手指,然后低声而严厉地问我是否已量过丧服尺寸了。
75

76

“你的衬衣呢?”默德斯通小一姐问,“你带回来了吗?”
77

78

这就是她那种坚定所给予我的全部安慰。我深信,在那样一种情形下,她很得意地显示她那种冷酷气质里的一切刻毒,她把这些称为是她的坚定、自制、意志和练达。她特别引以为荣的是她办事能力,现在她正持一付铁石心肠,把一切都用笔墨写下而以此来炫耀其能力。那一天余下的时间,以及后来的日子里,她从早到晚都坐在她那张书桌边,用一支坚一硬的笔嚓嚓写划,对每一个人说话都用那种镇静低沉的语调,脸上的肌肉没一丝松驰过,甚至她的衣着也没半点显示出慌乱。
79

她的弟弟有时拿起一本书,可我没见到他读过。他打开书,盯着书,好像在读,却整整一个小时没翻过书。然后,他放下书,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常合手而坐地看着他,数他的步子,就这样度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他很少对她说话,根本不对我说话。在那死寂的住宅里,除了那些钟,他就是唯一安定不下的了。
80

出殡前的那些天里,我几乎看不到皮果提,除了在上楼下楼时我总看到她在我母亲和那婴儿躺着的屋子附近,那就是每晚我上一床后她来到我身边,坐在我床头。在出殡的前一两天——我想是前一两天,不过在那段沉重的日子里,我觉得我是满脑乱成一片,根本没留心日子的消长——她把我带进那个房间。我只记得,在床上一种白色*罩单下,仿佛躺着这幢住宅的庄严寂静的化身,床四周美丽、整洁、清新。她要轻轻掀一开那罩单时,我叫道:“哦,别这样!哦,别这样!”
81

82

就算出殡是昨天举行的,我也不可能记得更清楚了。我一走进那间最好的客厅时,那屋里的气氛,旺旺的炉火,瓶中酒液的熠熠折光,杯盘的式样,糕饼的微微甜香,默德斯通小一姐穿的衣发出的气味,还有我们穿的黑衣,我都记得好清楚。齐力普先生也在客厅里,并过来和我说话。
83

84

85

“天哪!”齐力普先生柔和地笑道,眼中有什么东西亮闪闪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在我们身边长大了。他们长得我们都认不出了,小一姐?”
86

他后一句话是对默德斯通小一姐说的,但后者并不作答。
87

88

默德斯通小一姐只是做样子式地点点头,但皱着眉头,算是回答。受挫的齐力普先生握着我的手走到屋角,再也没开口说话。
89

我说出这一点,是因为我要说出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我只关注自己或回家以后关注过自己什么。现在,钟声响起,欧默先生和另一个人过来叫我们准备好。正好似很久以前皮果提就告诉过我的那样,曾送我父亲去那同一个墓地的人又在同一间屋里准备好了。
90

这一行有默德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普先生,齐力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杠夫和他们所抬的东西已来到花园里了,他们在我们前面走过花园小径,穿过榆树林,经过院门,来到墓地;夏日的早晨,我曾常在那里听鸟儿欢唱。
91

我们围着墓一穴一而立。我觉得那天好像和所有别的日子都不同,连陽光的颜色*都不同,是一种格外凄惨的颜色*。此刻,墓一穴一周围是我们和将入土安息的人从家里带来的肃穆和寂静。我们脱一下帽站在那里时,我听到教士说:“主说,我是复一活和生命!”他的声音在露天里听来似乎很奇特,但非常清晰明了。接着,我听到了呜咽声,然后我看到旁观者中那位善良忠心的仆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中,我最一爱一的是她;我那幼小的心中坚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她说:“做得好。”
92

在那一小群人中,有许多我熟悉的面孔,有我在教堂里看来看去时认识的面孔,有当年看到我母亲如鲜花初放时来到这村里时的面孔,可我并不在意这些面孔——除了我的悲痛,我什么也不在意——但我看到了这些并认识这些,我甚至看到我背后很远处站着的明妮,以及她朝她那离我很近的情一人飞送的眼风。
93

一切结束了,土填进去了,我们散开回去了。在我们眼前我们的住宅,那么漂亮,依然如旧,可在我年轻的心里,它和已失去的是联系得那么密切。于是它使我悲从中来,与它唤一起的悲痛相比,我一切其它的悲痛都不算什么了。可是,他们扶着我往前走。齐力普先生对我说话,到家后,他又拿给我一点水喝,我向他告辞回我的卧室去时,他那么温柔地和我分手就像女人一样。
94

正如我说的,这一切宛如在昨天发生的一样。而后来的许多事已飘往彼岸,将来,一切被忘却的事都会在那里重现,可是这一件事会像一块巨大的岩石站立在大海中。
95

我知道皮果提会到我房里来。当时那种安息日的寂静于我们俩都很合适(那一天那么像星期天!我已经忘了)。她坐在我小床上,紧一靠着我,抓住我的手,时而把我的手放到她唇边,时而用她的手来抚一摸,仿佛是在照顾我那小一弟一弟一样。
96

97

“她一直不舒坦,”皮果提说,“有好长一段时间都这样。她心神不定,也不快活。那小一毛一头生下来时,我以为她会好起来了。可她更虚弱了,,一天比一天差。小一毛一头出生前,她总喜欢一个人坐在那儿哭;小一毛一头出生后,她总轻轻对着他唱——唱得好轻,有一次我听到后都觉得那是天上的声音,是正在飘着远去的声音。
98

“我觉得她近来变得更胆小、更担惊受吓了;一句粗一暴的话于她就像一记拳头。可她在我眼里还是那样,在她那傻乎乎的皮果提眼里,她永远也不会改变;我那可一爱一的小姑一娘一是不会改变的。”
99

100

“我最后一次看到老样子的她是在那一晚,是你回家的那天晚上,我亲一爱一的。你回学校去的那天,她对我说:‘我再也不会见到我亲一爱一的宝贝了。’不知为什么我知道这事,这是真话,我知道。
101

“打那以后,她老想打起一精一神,每当他们说她没思想、不一操一心时,她总强打一精一神,但已没用了。告诉我的那一话,她从来没对她丈夫说过——她不敢对任何人说那事——直到一天夜里,也就是那事发生前一个多星期,她才对我说:‘我亲一爱一的,我想我要死了。’
102

“‘现在我心里轻松了,皮果提’,那天夜里我扶她上一床时她说,‘他会越来越相信了,可怜的家伙,在离到头不多的日子里他会一日比一日更相信了;然后一切都成为过去。我累极了。假如这是睡眠,那么在我睡眠时坐在我一旁吧,别离开我。上帝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吧!上帝看顾保护我那没有父亲的孩子吧!’
103

“那以后,我就没离开过她,”皮果提说,“她常和楼下的那两位说话——因为她一爱一他们,不一爱一她周围的人她就受不了——不过,他们从她床边走开后,她总转向我,好像哪儿有皮果提哪儿才能安息,否则她没法睡着。
104

“在最后那晚,她在夜里吻了我,并说:‘如果我的婴儿也死了,皮果提,请叫他们把他放在我怀里,把我们埋在一起。’(这都照办了,因为那可怜的小羔羊只比她多活了一天。)她还说:‘让我那最亲一爱一的儿子送我们去我们的安息地吧,并告诉他,他的母亲曾躺在这里为他祝福过,不只一次,而是一千次。’”
105

106

“那天夜里很晚了,”皮果提又说;“她向我要点喝的。她喝过后,朝我那么温顺地微笑,多可一爱一!——多美啊!
107

“天亮了,太陽正在升起,这时她对我说,科波菲尔先生过去对她多仁慈,多体贴,他多么容忍她,当她怀疑自己时,他告诉她说一颗一爱一心比智慧更好、更有力,在她心中他是一个幸福的人。‘皮果提,我亲一爱一的,’她又说道,‘让我挨你更近些吧,’因为她很虚弱了。‘把你那好胳膊放在我脖子下吧,’她说,‘让我把脸转向你,你的脸离我太远了,我要挨近你的脸。’我照她说的办了;哦,卫卫!我第一次和你分手时说的话可真应验了,这时候到了——我说过她喜欢把她那可怜的头放在她那笨头笨脑又坏脾一性一*的皮果提怀里——她就这么死了,像一个睡着了的孩子一样!”
108

皮果提的叙述就这么结束了。从听到母亲的死讯那一会儿起,她后来这几年的印象已从我心中消失了。从那一会儿起,我所能记起的母亲就是我最早印象中的她——常把亮亮的卷发绕在手指上,常在黄昏时和我在客厅里跳舞。皮果提所告诉我的一切,不但没让我重记起后来这几年的她,反越发使我早年印象中的她在我心中生下根来。这也许很奇怪,但却是千真万确。她死后飞回她那平静安宁,无烦无恼的青春中去了,其它的一切全被抹去了。
109

躺在坟墓中的母亲,是我孩提时期的母亲;她怀中那小人(就像我也曾躺在她怀中一样)和她一起长眠了,那是我。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