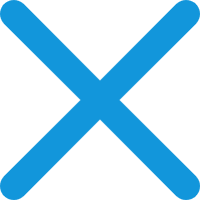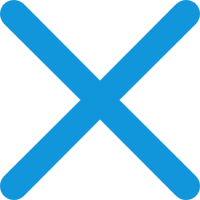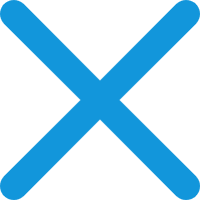让人们明白本书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别人,这是本书必须做到的。我的传记就从我一来到人间时写起。我记得(正如人们告诉我的那样,而我也对其深信不疑)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12点出生的。据说钟刚敲响,我也哇哇哭出了声,分秒不差哪。
1

我是在那么一天,又是在那么一个时辰出生的。对此我的保姆和一些大智大慧的女邻居是有个说法的。她们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起就对我投以无比关注了。她们说,我首先嘛,命不好,准多灾多难;其次,则有可以看见鬼魂的本事。她们认定这点:凡是星期五半夜后几小时内出生的婴儿都是不幸的。都具有那种禀赋,这是与生俱来的,男孩女孩都一样。
2

关于第一点,用不着我说什么了,因为只有我的亲身经历最足以证实那预言是否灵验。关于第二点,我只好说,要嘛可能是我还是个小一毛一头时就把那灵气用光了,反正迄今为止我还未体验到。不过,就是没那份灵气我也不会抱怨,如果别的什么人正享用这份灵气,我则衷心祝福他能终生享用。
3

我出生时带了一层胎膜①。后来,这胎膜就以15几尼的低价在报上登广告出一售。不知是当时航海的人手头紧,还是人们对这胎膜不存什么信心而宁愿穿软木救生衣,反正只有一个人报过价。这人是和证券经纪人打交道的律师,他报的价是两镑现金,不足部分则以雪梨酒抵偿。哪怕会因此失去永不溺水的风险担保,这人也不肯加一个子。最后只有撤了广告,白出了一笔广告费。说到雪梨酒,我那亲一爱一的可怜一妈一妈一自己也拿酒去市场上卖呢。十年以后,这胎膜由我们当地的50个人一抽一彩来决定由谁购买。每个一抽一彩的人先出半克朗,一抽一中的人则出5先令来买这胎膜。当时我也在场,看到自己身一体的一个部分竟如此让人处置,我心里真不好受,也窘得慌。我记得那彩是让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太一抽一中的。老太太十分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按规定应交的5先令,那全是一个个半便士的硬币,末了也还差两个半便士——虽然人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了很多算术方法向她说明这点,都没产生任何效果。后来,那一带的人好久好久还记得这个了不起的事实:这老太太的确不曾被淹死,而是在92岁高龄时得意洋洋地在床上咽了气。我听说她平生最得意地挂在嘴边吹嘘的事就是:她只走过一座桥,此外再也不曾在什么水上面走过。在喝茶时(茶可是她极其一爱一好的东西),她总表示对那些居然要游荡四海的水手和其它这类人的愤怒,她认为这种游荡简直是罪过。如果有人对她说人们正是因这种讨厌的行为才得到一些收获从而得到某些享受——如茶也可算是一种——那也没什么用,她总是更加有力更自信地说:“我们决不游荡。”
4

5

①英国人认为带胎膜出生者大吉。这胎膜可庇佑人不至溺水身亡。
6

7

我出生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就像苏格兰人说的那样是“在那一边。”我是一个遗腹子。爸爸闭上眼六个月后我睁开了眼。就是现在想到他竟从未见过我,我仍然觉得挺蹊跷的。而当回忆朦胧旧事时,更令我觉得奇怪的是,他那块白灰色*的墓石竟是我儿时最初产生的联想,每当我们的小客厅被火炉烧得暖烘烘,又被烛光照得亮堂堂时,我就对独自躺在黑夜里的父亲无限同情,想到他竟被我们关在门外,我简直觉得残忍不堪。
8

我父亲的一个姨一妈一——当然也就是我的姨一奶一奶一——是在我们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我后面还会谈到她——特洛伍德小一姐,或称贝西小一姐(当我可怜的母亲能鼓起勇气而提到她时总用后一个称呼,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这人长得漂亮但正如老话说的:“做得漂亮才算漂亮,”他在这一点上就不够漂亮了——因为他大有打过贝西小一姐之嫌疑,甚至在一次为日常饭菜争吵时,鲁莽到想把贝西小一姐从3层楼的窗口抛出去。他这些脾气暴躁的行为终于使得贝西小一姐给了他一笔钱,从此二人分开了。他拿着那笔本钱去了印度,而且根据我家中一个荒诞的传说,人们看到他在那儿和一个大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身上。可我总觉得,那应当是一个贵妃或是一个贵妃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才对。不管怎么说,十年后他的死讯从印度传来时,我姨一奶一奶一作何感想是无人可知的。和那人一分手,我姨一奶一奶一就恢复了她未嫁时的姓,并在很远的一个海边小村里买了间农舍,带了一个仆人去那里过独身生活。人们都知道她是从此要远离红尘了。
9

我相信她一度很喜一爱一我的父亲。可父亲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因为我一妈一妈一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蜡制的娃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一妈一妈一,却知道我一妈一妈一当时还不到20岁。自打结婚后,我父亲和姨一奶一奶一再没见过面。那时,我父亲的年纪是我一妈一妈一的两倍,他的身一体也不太结实。一年后,他去世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他去世后六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10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请原谅我竟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事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我本人的感官未获得任何印象。
11

当时,我一妈一妈一正坐在火炉边。她身一子虚弱,一精一神不振,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尚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好不绝望,楼上的一抽一屉里有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的祝词的针插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小婴儿的欢迎,欢迎他来到那个对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激动的世界上。就像我说的,我母亲在一个晴朗而起了风的三月下午坐在火炉边,胆怯怯,悲切切,十分怀疑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12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一姐,我母亲坚信这一预感。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在落日的余辉下,她步态生硬表情冷漠地走到了门前。
13

她来到屋前的举止又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我父亲常说,一般的基督教徒谁也不像她那样举止行一事。她没有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往窗里张望。她把鼻尖贴紧到玻璃上,她贴得那么紧,以至我那可怜又可一爱一的母亲说那时她的鼻尖变平而且成了白色*。
14

她使我母亲吃惊不小,所以我一心认为: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要感谢贝西小一姐呢。
15

我母亲惊慌失措,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一姐站在对面,扫视着屋里。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她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像惯于驱使驾驭奴仆的主人那样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16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想。”贝西小一姐说,那特别加重的语气大概是考虑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及心理状态才推断的。
17

18

“特洛特伍德小一姐,”来人说,“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19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她心头的不快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20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一姐说。我母亲低下头请她进来。
21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实际上,自从我父亲的丧礼结束后,那里的炉子就再没生过火。她们俩落座后,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哭起来。
22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一姐忙说。“别那样了!
23

24

25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掉,”贝西小一姐说,“让我看看你。”
26

这要求虽然不合情理,我母亲却实在太怯懦竟不敢拒绝,就算她心存怀疑也不得不照办。她只好照贝西小一姐的话做了,由于紧张,她竟把头发弄散全披到脸上来了。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
27

“唉呀,我的天!”贝西小一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28

毫无疑问,我母亲显得十分年轻,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显得年轻。她低下头,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可怜的人!一边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自己的确是一个孩子气的寡一妇,而且只要还能活下去恐怕还是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她停了一会儿,这时她恍惚觉得贝西小一姐在摸她的头发,并感到贝西小一姐的手并不柔和。可是,当她怀着怯生生的希望向贝西小一姐看去时,却发现这女士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盯着炉火。
29

“到底是怎么回事。”贝西小一姐突然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30

31

“为什么要叫它鸦巢呢?”贝西小一姐说,“叫它厨房要更合适些①,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概念的话。”
32

①鸦巢在英文里为Rookery与英文的厨房cookery一词音相近。
33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定的,”我母亲说,“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鸦巢。不过,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那些鸟早就不再来这里了。”
34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一姐大声说,“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周围一只乌鸦也没有,就把这房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不过是因为看见了鸟窝。”
35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居然当我面嘲讽他……”
36

我想,当时我那可怜又可一爱一的母亲真想打我的姨一奶一奶一。就算我母亲在那个晚上出手前受过专业的训练,姨一奶一奶一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一只手就降服她。不过,这场交手在她从椅子上起身时就结束了——她又乖乖坐下,因为她晕了过去。
37

她恢复知觉后,或是贝西小一姐使她恢复知觉后,她发现贝西小一姐站在窗前。暮色*更浓了,她们已彼此看不清对方。若不是炉火,她们根本就看不见对方了。
38

“嘿,”贝西小一姐回到座位上时说,就像刚才不过随意看了看风景一样,”你估计什么时候……”
39

“我浑身发一抖,”母亲艰难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40

41

42

“啊,啊,你认为喝茶会对我有好处吗?”母亲叫道,那模样真是可怜极了。
43

“当然有好处,”贝西小一姐说,“不过有些幻觉罢了。你把那女孩叫什么?”
44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一姐。”母亲天真地说。
45

“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一姐不禁引用了楼上一抽一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语,不过她不是对我而言,却是对我母亲而发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呢。”
46

47

“皮果提!”贝西小一姐重复道,十分忿忿然,“孩子,你是说居然有人走进基督教的教堂,然后自己又取了皮果提这么一个教名?”
48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说,“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用她的姓叫她。”
49

“嘿,皮果提,”贝西小一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
50

51

贝西小一姐发号司令那样子俨然像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一姐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52

“刚才你说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一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一出生……”
53

54

“我告诉你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一姐说,“别顶嘴。这个女孩一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做错事,不应滥用·她·的一爱一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监护,这样,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看做·我·的责任。”
55

贝西小一姐每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一挛似地摆一动一次,仿佛她旧日的过失仍在折磨她,而她要尽力克制着不流露出来。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一姐了,她太惴惴不安,也太软弱胆怯而茫然无措,所以她没法清楚地观察任何东西,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56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西小一姐又开口道,这时她的头也渐渐不再摆一动了,“你们一起过得快乐吗?”
57

“我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除了太好没别的了。”
58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想?”贝西小一姐紧跟着就这么说。
59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又孤身一人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一点来看,是的,我想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哽咽着说。
60

“行了,行了!别哭了!”贝西小一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般配的话——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61

62

63

“我在一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造访了那一家。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和蔼,对我特别关照,非常关心体贴,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一五一十地说。
64

“咳!可怜的小一毛一孩!”贝西小一姐沉思道,并依旧望着炉火皱眉头,“你知道点什么呢?”
65

66

67

“恐怕知道得不多,”我母亲答道,“不如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教我……”
68

69

“……我希望我已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当时学习的心情迫切,而他教得又很耐心,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没法往下说。
70

71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一言半语别扭,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3和5写得几乎没分别,或写7和9时加上了弯弯曲曲的尾巴,”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停下了。
72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西小一姐说,“你知道这一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非常不好。快别这样了!你决不能这样!”
73

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虽说她身一体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接下来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贝西小一姐间或发出一声“咳”打破这沉默,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
74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我知道”,过了一阵,,贝西小一姐又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
75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76

77

78

79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一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一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80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皮果提从没听说过我姨一奶一奶一这人,而我母亲也没提起过她。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并不住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81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下来了。发现对面坐着这么一位陌生女子,又推想可能会这么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医生就——我猜想——努力表现得有礼貌并善交际。在他那个一性一*别中,医生可算是最举止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顺随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总侧着身一子走路,唯恐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么轻柔,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谦卑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说过什么无礼的话,那还不算什么了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不会说什么厉害话的。他对疯狗也只会和顺地说一句,或说半句,或仅仅说几个字,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他走路那样慢。他决不会对一条狗粗一暴,他决不会对一条狗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82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一奶一奶一,头歪向一边向她微微鞠躬致意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说的是那些珠宝商的棉球道:
83

84

“什么?”我姨一奶一奶一把那些棉花一下子像拔一个塞子似地拔了出来。
85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种粗一暴吓了一跳——他后来告诉我母亲说——差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仍然温和地重复说:
86

87

齐力普先生这下再也不好干什么了,只得坐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着,直到人们请医生上楼去。医生在楼上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又下来了。
88

“怎么样?”我姨一奶一奶一把靠近医生那一侧耳朵里的棉花扯出来问道。
89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呢,夫人。”
90

“呸……!”我姨一奶一奶一发出这个表示蔑视的字眼时还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又把自己耳朵像先前那样塞了起来。
91

的确——的确——齐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说,他几乎要吓得闭过气了,从职业的观点来看,几乎闭过去了。可他当时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了近两个钟头,直到人们又一次把医生请上楼。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92

“怎么样?”我姨一奶一奶一把那侧耳朵的棉花扯出来后问。
93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94

“嘘……!”我姨一奶一奶一只发出这种声音。这种无礼的待遇使齐力普先生觉得绝对忍受不了了。他后来说这简直是存心让他一精一神崩溃。在人们再来请他之前,他宁愿坐在又黑又当着风口的楼梯上。
95

第二天,汉姆·皮果提报告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碰巧又在客厅门口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被正激动得踱来踱去的贝西小一姐瞥见并一下抓住了,他这下可没法跑掉了。汉姆进过免费的国民学校,对教义问答回答得挺不赖,所以可以算是靠得住的证人。他说,楼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和其它声音,当这些声音变得很大时,那女士就一把把他揪住,把他当作供她渲泄过剩的激动的出气筒那样;他说,据此可以推断,那些棉花并不能挡住楼上的声音。他还说,那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用了太多的鸦片酊一样。女士摇晃他,抓乱他的头发,一揉一皱他的衣领,塞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他的耳朵和她自己的耳朵一样,还抓他,打他。他自己的姑一妈一证实他以上所述属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她刚被释放的时候——看到他,声称他当时和我一样那么红通通。
96

就算温顺的齐力普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怀有恶意的话,在那时也不可能了。他刚忙完,就侧着身一子走进了客厅,非常和蔼地对我姨一奶一奶一说:
97

98

99

我姨一奶一奶一这种极其严厉的样子又把齐力普先生吓懵了。为了让她温和一点,齐力普先生向她微微鞠了一躬,又微微笑了一笑。
100

“天啊,这人到底怎么了?”我姨一奶一奶一不耐烦地叫道,“他不会说话吗?”
101

“冷静点,夫人,”齐力普先生用他最温和的口气说,“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夫人,冷静吧。”
102

打那以后,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件奇迹——我姨一奶一奶一居然不去摇晃他,不去摇晃他一逼一他把话说出来。她只对他摇了摇自己的头,不过那模样也让他够怕的了。
103

“哦,夫人,”齐力普先生感到鼓足了勇气马上说,“非常高兴地祝贺你。一切都好了,夫人,圆满地结束了。”
104

齐力普先生投入地做了五分钟左右的演说时,我姨一奶一奶一仔细端详他。
105

“她怎么样?”我姨一奶一奶一抱着双臂问,其中一只胳膊上还挂着她的帽子。
106

“哦,夫人,她马上就会觉得很舒服了,我希望那样,”齐力普先生说,“在这种凄惨的家庭状况下,对任何一个年轻母亲我们能期待的舒服也不过如此。夫人,如果现在要去看她就请去吧,那只会对她有益。”
107

108

齐力普先生的头歪得更厉害了。他看着我姨一奶一奶一样子就像一只乖乖的鸟。
109

110

“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那婴儿是个男孩。”
111

我姨一奶一奶一二话没说,拿起帽带好像拿着一个投石器似地对着齐力普先生头部瞄了一会,然后把帽子朝自己头上歪扣上,便一去不返了。她像一个失望的仙女那样消失了。或者说像人人都认为我有本事看得见的鬼魂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
112

她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我睡在我的摇篮里,我母亲睡在她的床上,而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德则永远留在了那片梦想和幻想的地方,那片我不久前还游历过的广袤区域。照在我们卧室窗户上的光亮也照在这世间过客最后安息的地方,也照在那不属于那个没有他就没有我的残灰尘土上。
113